談談音樂論文如何選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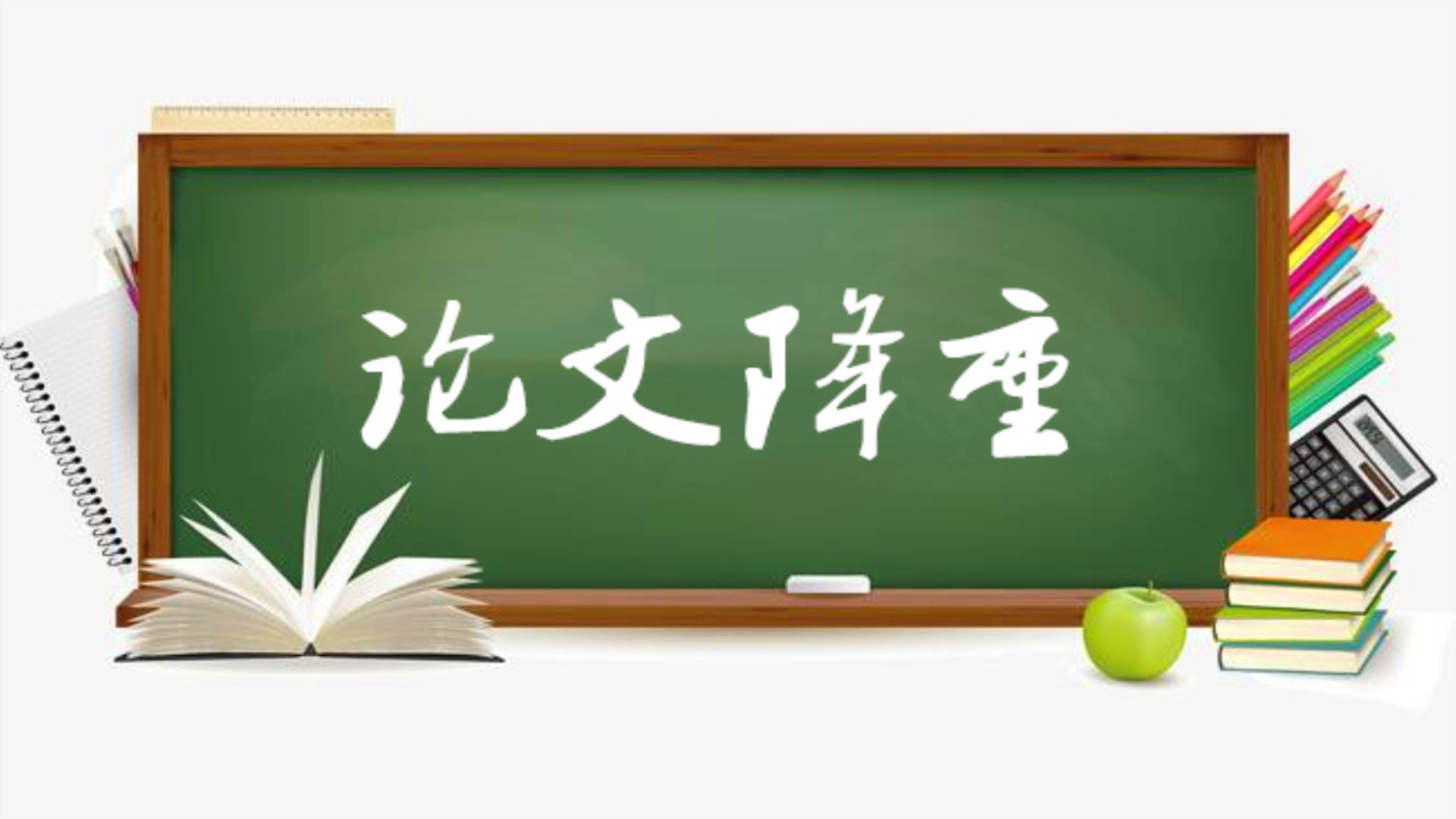
音樂論文是藝術論文的一種,常見的音樂論文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案例分析,選擇一首作品,進行鑒賞研究,例如《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一種是理論研究,從理論的角度探討音樂學相關問題,例如《論蘇聯音樂思想對中國音樂理論的影響》;還有一種是實踐分析,這種方式多應用在音樂教學類論文中,從實踐出發,得到結論,例如《云教育平臺模式在高校音樂理論教學中的應用》。每一種類型的研究方法、寫作要點都不相同,在選題時基本已經確定。本文主要探討音樂論文如何選題。
一、以小見大,從細節出發
對于“小題大做”還是“大題小做”的問題,向來仁者見仁、莫衷一是。但是,筆者認為,對于那些尚處在摸索階段的作者而言,前者顯然是更為明智的選擇。下面是筆者從來稿中隨意選取的幾個典型的過“大”的選題,例如《黑格爾音樂哲學的藝術本質》《基督教音樂源流考辨》《談我國近代的聲樂教育發展》等。雖然所謂的“大”“小”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顯而易見,上述選題所探討的內容起碼要碩士乃至博士論文的篇幅才能容納。而且,除非作者在相關領域浸淫多年,有著深厚的學術積累,否則以萬字左右的篇幅來探討這些問題,其結果必然內容空泛蒼白,言之無物,多是一些常識性理論和知識的歸納,缺乏基本的學術創新。且不論作者是否有能力駕馭這些宏大的選題,單從操作層面看,過于大的論域往往會對寫作者的知識儲備、資料搜集、論據充實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無形中使得寫作難度成倍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剛開始嘗試理論研究和寫作的人,越容易選擇這種費力不討好的選題。這跟人的認識規律有一定的關系,通常我們在學習和接觸一個新的學科或者知識領域時,往往會從一些基礎性、概括性的角度入手對其加以認識。如果對于自己的研究課題只是一知半解,就開始急于構思選題,難免會根據自己尚為粗淺的認識選擇一些基礎性、規律性的問題進行理論性的思考,殊不知這些思考往往帶有很強的共性,也就是說,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同樣的論題,于是選題撞車就在所難免。而且越是基礎性的理論問題,越會有相關領域的專家予以關注,相應的研究成果也就更多。因此,對于一位初步接觸某一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建議最好不要倉促動筆寫作,一定要深入再深入,直到能夠把握住一些有學術價值、有創見的細部問題進行探討。那種閉門造車、重復做工的情況,應該盡量避免。
對于這一原則的運用,最有代表性、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于潤洋先生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這篇文章在對瓦格納這部經典作品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打破了以往慣用的研究模式,將對音樂本體的分析放在了作曲家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大背景中加以闡釋,使得研究的視角更廣闊,對藝術作品的分析更深刻,對作品的思想內涵揭示得更幽深精邃。其更為深遠的價值還在于,通過這一部作品的分析,不僅生動地闡釋了作者所倡導的“音樂學分析”的音樂本體—社會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同時作者也以自己的分析為后學提供了一個經典、鮮活的研究范本。“音樂學分析”的提出對中國的音樂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代音樂學者因此受益。
量力而為、小題大做是音樂論文寫作中一項重要的原則,在做碩士乃至博士論文選題時同樣適用。一旦遇到因論域過大而感到駕馭吃力的選題,我們可以采取逐步縮小、次第限定的方式,在時間、空間上對論題加以限定。這里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如前面提到的《談我國近代的聲樂教育發展》,如果我們覺得選題有些大,可以在時間上對其加以限定,將選題改為“試論我國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聲樂教育發展”;如果這樣還是覺得不好把握,可以進一步縮小論域,將論題改為“試論我國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專業聲樂教育發展”。這樣在不改變選題方向的前提下,論域更加集中,寫作難度也會有所降低。
從某種意義說,沒有不能做的選題,關鍵是看你有沒有掌控這個選題的能力。例如關于合唱與和諧社會的關系、中國音樂學發展現狀這些看似很難把握的問題,在專家的筆下同樣可以闡述得高屋建瓴、言之有物。如田玉斌的《合唱和諧——談合唱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功能與作用》、于潤洋《關于音樂學研究的若干問題思考》。
二、選擇新方法、新領域
這里的新與舊都是相對而言的。所謂“舊”,是指已有研究成果較多,較難發現創新點的研究領域,或者是自己駕馭起來有一定困難的選題。以西方音樂史為例,從巴洛克時期一直到近現代歐洲音樂各個新潮流派的研究,我們能搜集到的從經典教科書、個人專著到單篇的學術論文可謂是汗牛充棟。如果沒有新觀點的提出、新史料的發現,而僅靠外文文獻的翻譯,或對現有史料的歸納梳理,不僅違反學術研究的創新原則,更有悖于基本的學術規范。而相對來說,國內對于巴洛克以前的中世紀時期甚至更早的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音樂的研究成果則較為缺乏。
而所謂“新”,筆者以為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的內容:
第一,新理論、新方法、新體系、新觀點的提出。這是學術研究中最為艱難,但也是最有創意并最令人興奮的部分,雖非一般的研究者所能做到,確是每一位有志于從事音樂理論研究的學者畢生追求的目標。要達到這種目標往往需要研究者的學、識、才兼備,即有深厚、扎實的學術功底,敏銳、深邃的學術洞察力以及對當下音樂歷史發展趨勢的準確、前瞻性把握。除了前面提到過的于潤洋先生《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的例子,由李西安發起,翟小松、葉小鋼、譚盾等人參與的《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案例。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對話錄的形式呈現,但因記錄了改革開放初期,剛剛崛起的一批“新潮音樂家”創作理念上的探索與碰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示出極大的開創意義,因而成為記錄新時期中國音樂歷史發展的重要文獻。今天,這篇文章發表已經近三十年,當時參與談話的幾位作曲家都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音樂創作的中流砥柱,在國際樂壇上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作為發起人和提問者的李西安在其中所表現出的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深遠的歷史意識愈發顯得難能可貴。
其二,對新音樂作品、音樂現象、音樂家以及新的唱片、書籍的評介。閻寶林、周振宇的《虛擬合唱在互聯網上的現代呈示——實現所有熱愛合唱者的夢想》一文,就是這種創新型選題的代表性例子。在很多人(包括業內人士)還不知道“虛擬合唱”為何物時,作者已經對這個誕生于網絡時代的新穎的合唱表演形式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通過對其產生的標志性事件、基本運作形式和種類以及其與傳統實體合唱團的比較,揭示了它為傳統的合唱概念所注入的全新的涵義。從而使網絡發展為當代音樂生活所帶來的深刻變革添加了一個生動而具體的注腳。
其三,對于一些“傳統選題”要善于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思路、理論,從而使其產生新的時代價值。
這類文章有一個例子就是楊健的《西方音樂表演中有關rubato問題的傳統觀念與實證研究》。一直以來,我們對于rubato的理解,多在肖邦、李斯特等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中,但實際上,在19世紀乃至整個20世紀的歐洲音樂表演領域,這種表演原則被廣泛運用到不同時期的音樂作品中。作者通過對包括《新格羅夫詞典》在內的西方經典文獻中有關此項研究的梳理,敏銳地把握住了rubato在表演實踐中盛行、但主流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看法仍顯得非常主觀而模糊的現狀。進而,通過自己設計的“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方法”及編程的相關軟件對20世紀一些經典演奏版本中有關rubato的處理進行了對比分析。借助先進的科技手段,原本只能依靠感性感知的音樂表現方式得以具體、直觀的量化,從而為當代的音樂藝術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王惠芹的《哈利姆?埃爾-達巴鋼琴組曲〈大宇宙藝術中的小宇宙〉(ⅰ—ⅲ)研究》則嘗試將世界音樂的視角和研究方法與西方現代音樂技術分析的方法結合在一起。文章從宏觀的創作理念、具體的音樂構思和調式結構等層面對埃及裔美國當代作曲家哈利姆?埃爾(halim el-dabh,1921—) 的作品進行了全面分析。同時,借助尼日利亞學者阿金?尤巴所倡導的“非洲鋼琴主義”理論模式,揭示了作品與埃及傳統文化的聯系、蘊含非洲特征以及與西方后現代主義的作曲技法有機地融合。阿金?尤巴的這一理論雖然是誕生于歐洲- 非洲語境下的研究理論,但對于同樣處于歐美強勢文化籠罩下的中國當代音樂研究亦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對于新創作的音樂作品、新出版發表的理論研究成果以及當下音樂生活中的熱點話題評介與探討也是不錯的選題,但在選擇這類選題時,應注意其應有較高的藝術水準和學術價值,能夠反映出當前創作、研究的某種潮流或趨勢,對于新問題的把握,當然并不能因為“新”,就只做介紹和翻譯的工作,缺乏學術論文所必要的研究性。這類選題同樣要求我們對于相關領域的成果有著必要的了解,因為沒有一個學科是憑空出現的,都是建立在該學科領域已有的成果基礎之上的。
三、另辟蹊徑,選擇研究少的“冷僻”話題
所謂以偏代正,與以新代舊的思路有著相似之處。大多是在傳統研究領域中,作者能夠獨辟蹊徑從那些相對較少人關注的問題入手,展開自己的研究。相比對整個專業發展有著全面的了解、宏觀的把握作為研究基礎的要求,這類選題往往更看重作者是否在某個領域中有著人所不及的深入了解。因而,對于很多從事表演專業的人來說,他們多年積累的藝術實踐經驗為他們撰寫論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但這類選題往往容易被忽視,因為缺乏理論思維和寫作的習慣,往往被大家視為一種習以為常的東西而忽視掉了。所以,當我們放下樂譜拿起文稿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追求、模仿理論家的思維和寫作方式,從而失去了自身得天獨厚的知識優勢。
例如,在民族音樂研究領域,除了二胡、琵琶、古箏等這些發展較早、學科體系完善,人才輩出、作品也較多的專業,贏得了眾多理論家、作曲家的關注,在其發展歷史、樂器沿革、作品研究、教學理念、演奏技法等等方面都有著很多研究成果;相對而言,笛子、揚琴、三弦、阮、笙等規模較小的專業,相關的理論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尚有很多可做文章之處。如范元祝《20世紀笙的改革與笙曲創作》。這篇文章的整體結構,采用了其他民族樂器發展歷史脈絡上的一些共性思路,但因其在這個大框架下探討的是笙的改革與創作歷程,內容翔實、豐富,依然不失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龔航宇《關于格倫?古爾德鋼琴演奏中“怪癖”現象的思考》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眾所周知,格倫?古爾德是20世紀最具個性的鋼琴家之一,他不僅以其獨樹一幟且令人嘆服的演奏風格而著稱,還因演奏中坐得很低、手型扁平、愛脫掉鞋子錄音、大聲地哼唱、喜歡邊演奏邊用手指揮等等“怪癖”而被樂迷和媒體津津樂道。本文的可貴之處在于,作者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簡單地將這些“怪癖”視為嘩眾取寵、博取關注的噱頭,而是通過有理有據的分析深刻地指出這些“怪癖”都是演奏家為了完成自己個性化的藝術表現,而突破世俗的觀念所做出的恰當、必然的選擇。如文中指出,坐得低可以“使得手臂的重量更好地沉下來集中到手指上,更有效地減少在只需手指本身運動時手臂的用力,最大限度地節省了消耗……”想人所未想,見人所未見,不僅成就了這篇頗具可讀性的文章,也為我們反觀在鋼琴演奏中被視為金科玉律的規則,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參照。
這里所說的新的空白點,有一個時間、空間的差,也即是對我們的知識結構具有拓展意義的選題,下面筆者舉兩個例子:郭玉的《“天才”亦需“成長”——從莫扎特交響曲的管樂配器看其音樂風格發展軌跡》和潘達的《莫扎特歌劇〈魔笛〉中的“3”原則》。前者摒棄了以莫扎特的生平事件以及他在多種體裁領域中所共同體現出的音樂語言風格特點為依據的籠統劃分其交響樂創作分期的方法,而是從“交響曲中的管樂配器”這個特定體裁的特定方面來審視其交響樂創作歷程的嬗變,為我們了解這位古典作曲大師交響樂創作風格的發展與革新,提供了一個更為細致、更為有趣的脈絡線索。后一篇文章則把國內相關研究中,因歷史文化差異較少涉及的宗教文化背景,引入到對莫扎特歌劇創作特征的分析中。雖然關于莫扎特的各類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但是兩位作者還是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長,成功地尋找到了富于新意的研究選題,為我們認識莫扎特的音樂創作提供了新的視角。
從事表演專業的作者寫作這類選題,可能在原始資料特別是實踐的、感性的經驗上占有一定的優勢,但對于基本寫作技巧則有所欠缺,以一種理論化的思維對這些材料進行理性思考、梳理以及詮釋則是一個需要長期訓練的過程。堅持不懈,假以時日,不難寫出具有獨特學術價值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