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自然保護區發展新途徑之自然教育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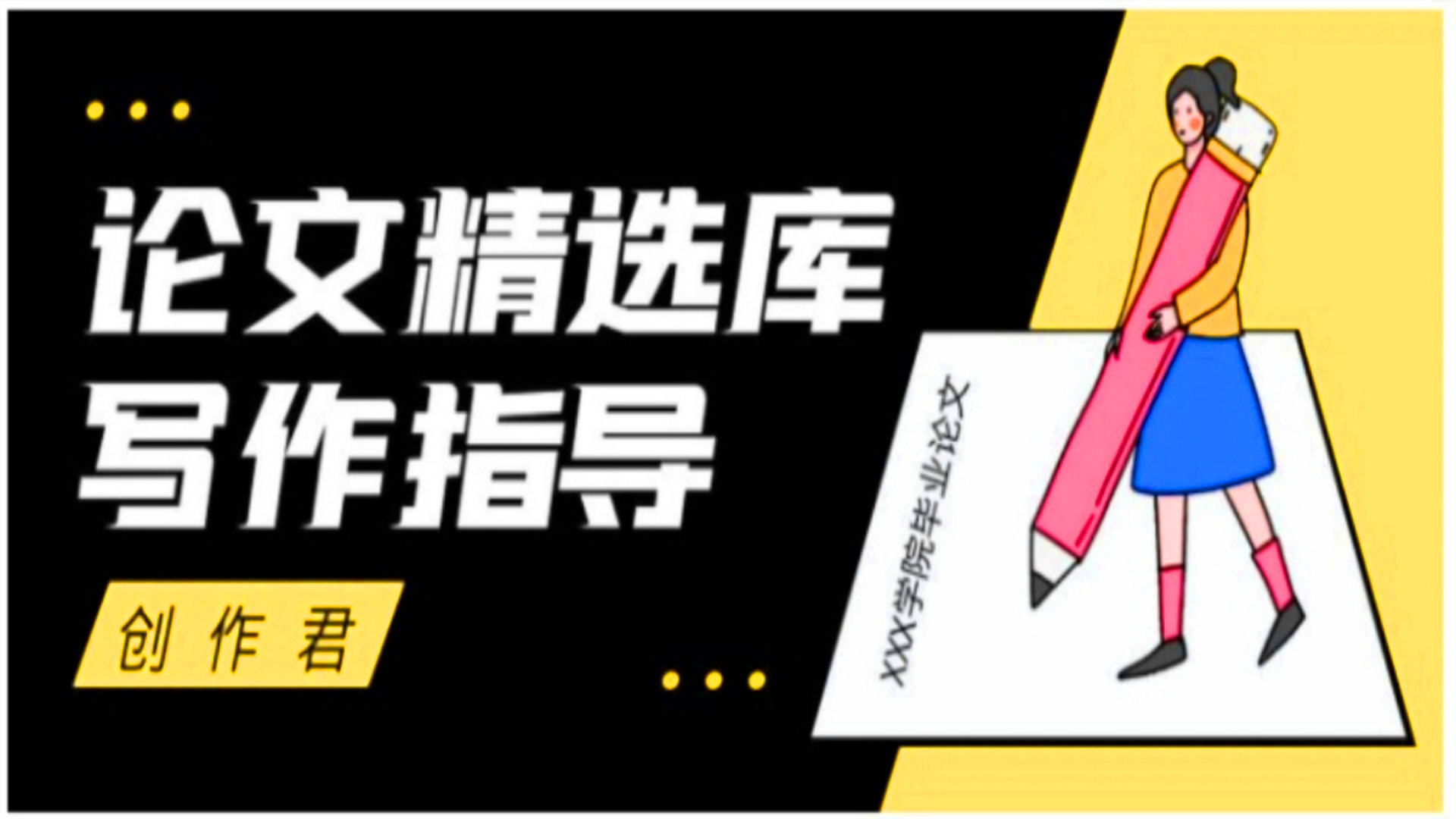
本文是一篇職稱論文,文章以國內保護區自然教育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綜述、歸納推理等方法,梳理自然教育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和國內保護區自然教育的研究進展,探討保護區如何利用自然教育轉變發展方式,以期為今后保護區開展自然教育工作提供參考。
1 國內自然教育實踐
1.1 發展歷程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自然教育研究始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20世紀70年代是我國環境教育和自然教育起步的重要時期,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大力開展環境保護的科學研究工作,做好宣傳教育”,就此拉開了我國自然教育的序幕。20世紀80年代開始,環境教育課程已被納入我國中小學教育的課程范圍,學校通過環境知識教育引發孩子們對環境的思考并提高環境保護意識。環境教育在國內的探索實踐,為人們了解自然、走進自然提供了契機,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人地關系。國內對自然教育的研究最早始于1983年,然而在2010年以前基本上是討論國外的自然教育思想。2010年《林間最后的小孩》在中國出版,書中出現的“自然缺失癥”這一概念引發了國內社會對兒童心理和生理的關注,帶動了自然教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在新時代的旅游業態下,自然教育的需求在逐步增加,其發展潛力巨大、前景遼闊,亟需高質量的自然教育基地推進自然教育產業的穩步發展。
2014年,環境保護部宣傳教育中心啟動“國家自然學校能力建設項目”,開始自然教育場所試點工作。同年第一屆全國自然教育論壇在廈門舉辦,隨后每年舉辦一次,為自然教育行業提供交流探討、信息互通的平臺,自然教育逐漸被廣泛認知。與此同時,自然教育機構也呈現出“井噴式”發展,形成公益事業與產業相互交融的模式。而當民間自然教育出現蓬勃之勢時,如何使自然教育的開展規范化、科學化、系統化,為自然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引導和支持。2019年4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布的《關于充分發揮各類自然保護區社會功能,大力開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推動了自然教育的快速發展。同年10月,中國林學會發布了《森林類自然教育基地建設導則》等團體標準,政府與民間的大力推廣已經成為推動自然教育行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即便已經發布了國家及地方自然教育的團體標準、導則、指引等,但因缺少自然教育法律法規的保障而產生了很多阻力,給自然教育的實踐工作帶來一定困難。
1.2 自然保護區自然教育研究進展
近5年來,自然教育的文章逐年增多,但在研究自然保護區自然教育方面的文章卻寥寥無幾。筆者以“自然保護區和自然教育”為主題在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僅搜索到30余篇相關文章,最早的一篇發表于2018年,是關于陜西長青自然保護區開展自然教育的文章,此后于2019年發表1篇,2020年發表9篇,2021年發表11篇,2022年發表13篇。從內容來看,現階段保護區自然教育的研究還存有大量的空白。
呂來新等從森林資源、基礎設施、人才隊伍、安全保障、特色課程等方面對黑龍江涼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提出策略;姚晨心等以安徽揚子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從主體與內容規劃、分區規劃、課程規劃等方面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保護區自然教育模式。張翠霞以內蒙古大青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自然教育為研究對象,從基礎設施、自然教育課程、自然教育人才、社區參與及資金支持進行路徑探析。劉俊等通過對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經營性自然教育活動和公益性自然教育活動的現狀調查評估,提出自然保護區在周邊社區開展公益性自然教育活動是極其必要的。蔡家奇等以石首麋鹿保護區自然教育為例,分析了自然教育體系建設的方式。邵飛等圍繞機構設置、品牌建設、新業態培育、基礎設施和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分析評價山東省各類自然保護地自然教育現狀。陳曉晴等以天目山和清涼峰自然保護區為例,對野生木本觀果植物資源進行了自然教育價值評價分析。綜上來看,目前對自然教育的學科融合、品牌建設、營銷策略及社區參與模式的探究還較少。
2 國內自然保護區開展自然教育的特殊性
2.1 保護對象的特殊性
自然保護區是為了保護珍貴、稀有的動植物物種及其原生地、棲息地,或是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的生態系統、自然遺跡、自然景觀等而建立的,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是自然教育的主要活動場地。自然保護區根據保護對象分為生態系統類型保護區、生物物種保護區和自然遺跡保護區3類。自然保護區不僅可以保存較好的原始生態環境,防止自然資源被破壞,而且為生物物種的繁衍與棲息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對維持生態平衡具有重要意義。和城市內的動、植物園不同的是,為了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自然保護區的人為痕跡較少,生物種類繁多,而其豐富的本底資源是開展自然教育的天然優勢,可以使受教育者進一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并且對保護對象有更深層次的了解,而不是對其停留在圖片或文字的初步印象。沉浸在自然環境中有利于激發受教育者反思自我,提高保護環境的意識,建立人與自然生理及心理的聯結,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從而達到自然教育的目的。
2.2 保護方式的特殊性
自然保護區是為了確保林業資源的完整、有效地維持生態平衡而成立的,被劃分為核心區、緩沖區及外圍區3部分。核心區禁止一切干擾;緩沖區只能從事科學研究觀測活動;外圍區即實驗區可以用來進行多用途活動,是進行旅游開發的重點區域。3個分區的規劃不僅保護了生物資源的完整性,還可以充分發揮自然保護區的社會功能,如科普教育、休閑娛樂等,實現多方參與、利益共享。隨著人們生態文明意識的提高,自然保護區的價值已經被廣泛認可,而自然教育不僅可以使公眾獲得親近自然、感受自然的體驗,而且可以將生態保護、生態游憩與生態體驗融合在一起,延伸自然保護區的價值。自然教育可以體現保護區保護與發展的理念,在生態承載力的范圍內以及不影響自然資源保護與科研任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利用保護區的自然教育資源,在外圍區適當建設自然教育基地、科普中心、自然教育課室等相關設施發展旅游業,達到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因此,開展自然教育是自然保護區在功能上的延續,是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2.3 管理體系的特殊性
我國自然保護區建立的時間較晚,由于早期主要是搶救性保護,相關土地用途及權屬的規定不完善,部分自然保護區缺乏細致考察,出現范圍及功能區劃分不合理、界限不夠清晰等問題,導致保護區的管理嚴重滯后于生態文明建設需求。從體制上看,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責交叉、權限分散,各主管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管理關系混亂。部分自然保護區也未落實相關條例,仍存在多頭管理現象,難以協調相關權責和利益,管理效率低下。從人員上看,保護區占地面積大,進行巡查、科研、監測等任務繁重,但是各保護區相關工作人員嚴重短缺,現有的工作人員大多沒有經過專業培訓,缺乏專業素養,技術力量薄弱,保護區各類數據不能及時更新,導致存在本地資源不清、資料斷層等現象。從經費上看,自然保護區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支持,但是目前各級政府僅能支持日常人員的經費開支,而在科研工作、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我國近幾年逐漸重視保護區體制機制的改革, 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其中進一步明確了自然保護區的定位規劃、管理體制、建設發展、監督考核及保障措施,為自然教育的開展奠定了體制基礎。而自然教育的開展反過來為保護區解決經費不足的困境,同時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保護區的建設意義,提高保護區在社會面上的影響力。
3 利用自然教育開辟發展新途徑
3.1 形成自然教育地方特色
自然教育的根本是自然,自然教育必須依托大自然環境進行。由于自然保護區的特殊性,每一個自然保護區的地域特色、生態系統、保護對象不盡相同,在利用自然教育尋找發展新途徑時,首先要做好清晰的定位,立足當地環境,熟悉本土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如森林植被、古樹名木、野生動植物、地質地貌、特色中草藥資源等,人文資源如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紅色文化等),參考當地的發展現狀開發獨有的自然教育課程、自然教育徑、自然教育書籍、自然教育文創等自然教育產品,探索出具有本地特色的自然教育管理和服務模式,突出自然性、地域性、群眾性。例如廣東車八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利用區內的特色水文、動物、植物等自然資源以及瑤族文化、紅色文化等人文資源,根據各個區域的特點,設計出體現資源特色的自然教育科普路線,以夏令營、自然課程、自然觀察、徒步等方式開展自然教育活動,開發了“一館二道三園四堂”的科普教育體系,逐步形成具有車八嶺特色的自然教育科普體系。
3.2 搭建自然教育合作平臺
以自然教育為合作紐帶,建立活動平臺、拓寬合作領域,增強保護區在社會面的輻射力,以此助力基地自然教育工作持續高效發展,形成多方協力的自然教育推進機制,進一步深化及推廣自然教育在社會面的影響力。我國部分自然保護區已經通過與各類團體展開合作,形成“保護地+學校+機構”的自然教育實踐模式,不僅帶動社區發展、實現農民增收,還可進行資源保護。保護區內的科研資源豐富,而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力量雄厚,通過搭建自然教育科研平臺,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科普宣教和科研監測等相關項目、組織保護區工作人員進行交流學習,可以提高保護區在自然教育方面的科研能力,填補保護區在技術方面的空白,同時也可以通過合作擴大保護區的資金來源,實現雙方互利共贏。
3.3 打造自然教育社區生態圈
自然保護區的發展離不開周邊社區的支持。保護區與社區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雙方利益未能達成一致。就保護區而言,它的職責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對區內資源進行監測以及預防自然災害的發生,保護生態環境不被破壞,追求生態效益。就社區居民而言,由于他們一直以來進行著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保護區內的資源依賴性較強,再加上陳舊的思想觀念,還沒有樹立保護資源的意識。
將自然教育實踐與社區發展進行深度融合,定期向居民宣傳自然資源保護與利用的知識、組織自然教育講座、鼓勵當地居民積極參與保護區的自然教育事業、共享自然教育帶來的收益成果,如建立自然教育產業反哺機制,促使社區參與到自然教育以及生態保護工作中,將“綠水青山”真正轉化為“金山銀山”。通過當地居民的主動參與,可以更好地發揮地方優勢和傳統,實現多元主體利益平衡,推動形成一個自然教育社區生態圈,使居民自覺形成保護環境、愛惜資源的意識,有效地減少“偷伐偷獵”現象。例如,平武縣關壩村形成“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教育發展模式,即以關壩旅游合作社為主體,在主管部門和村兩委的監督與管理下,通過與村外自然教育機構和社會組織合作支持開展自然教育,在利益分配方面,合作社通過二次分配實現全村收益,促進社區發展。再如,丹霞山依托自然教育,形成集戶外考察、科普場館和科普學堂不同類型的產品服務系統,并通過開展導師培訓、本地科普志愿者訓練營等培訓交流活動,將社區居民培育成科普導師、科普導賞和科普志愿者,以科普產業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丹霞山社區建設。自然教育將成為緩解自然保護區與當地社區生計之間的沖突、推進保護區與社區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路徑。
4 結語
自然教育在我國已經愈發受到重視,時代的進步促使人們從物質滿足轉向精神文化需求,而保護區自然教育的發展無疑為這樣的需求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在經歷了疫情肆虐,病毒橫行之后,不難發現不僅人與人之間是共同體,人與自然更是。從人與自然的思考中關注人本身,是自然教育存在的重要意義。走出城市,回歸自然,不僅可以引導人們關注自然、形成保護自然的意識,還可以改善生理或心理狀態。這樣的機遇也是保護區能夠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解決保護與開發的轉折點,開展自然教育可以充分發揮其科普教育、宣傳自然的社會功能,最后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一終極目標,進而形成雙向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略)
本文收集整理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



